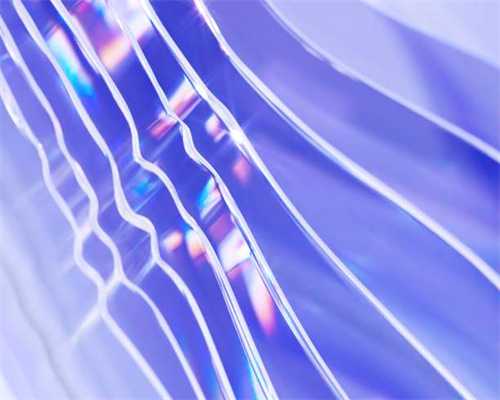1947年的夏济安(左)、夏志清
主题: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时间:2021年5月7日
地点:上海复宣酒店
嘉宾:陈思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王德威哈佛大学教授
主持:季进苏州大学教授
主办: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教给我们从艺术上
肯定文学作品的方法
季进:经过紧张的筹备,“夏氏书信和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坊召开了。今年是夏志清百年诞辰,正好夏氏书信五卷本全部出齐,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致敬夏先生,探讨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洞见,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愿景和问题。
陈思和: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学者,我是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在海外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受益者。以前海外汉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很少(除了东欧有一点),直到夏氏兄弟他们的努力。我很早就读了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我很惊讶,一个海外的学者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左右文学的研究,而且研究当中的很多成果后来都被我们采用。
夏志清先生1983年到过复旦,那是他唯一一次到中国大陆来。他跟我们中文系王纪全先生是亲戚,当时应钱锺书先生的邀请到中科院访问,然后顺道到复旦。贾植芳先生参与了接待,把它记到了日记里。率先在上海接待夏志清先生,复旦大学也是开风气之先。
我对夏氏兄弟海外汉学的成就稍微讲几句话。因为关于夏氏兄弟尤其是夏志清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争论纷纭不断。我读《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在争论当中,我从贾先生那儿看到这本书,后来托人到海外买回来。在上世纪80年代他起到的作用,今天的年轻人是不能想象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在今天的文学研究是面临非常多元的格局,各种文学史的版本,各种文学史的内容,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对我们产生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其中的一种观点。在今天来说,完全可以挑剔里面哪些讲得好,哪些讲得不好。而在上世纪80年代,它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印象中夏先生原来是搞英国文学的,从欧洲文学经典的角度挑选现代文学,他认为他挑选出来的是艺术上过得硬、写得好的,他不挑的就是不好的。他的标准跟我们之前所受教育中的标准完全相反,我印象很深。
我们现在一般讲夏先生是“捧”了张爱玲、沈从文,其实他在文学史上给很多作家很高的评价。我印象当中他写了鲁迅、张天翼、吴组缃这一类左翼作家,写了沈从文的乡土民间道路,写了张爱玲的都市民间道路,然后讲了钱锺书的《围城》,讽刺知识分子的题材。这四大方面中,除了都市是现代文学发展当中一点一点产生出来的新题目,其他的乡土文学、左翼文学、知识分子讽刺文学,在当时是几个大的方面。讽刺小说,在鲁迅《彷徨》中的很多小说里找得到渊源;乡土小说,鲁迅的《故乡》开创了道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我们看到一个由左翼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知识分子讽刺题材这样四大方面组成的文学史的格局。
而当时我们主流观点所接受的是只有一个格局,而且还是残缺不全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五四+鲁迅+样本戏+《金光大道》等,其他文学史上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正面面对。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现代小说史》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对我们大陆的文学研究启发是非常大的,这是我很直接的感受。它教给我们一种从艺术上来肯定文学作品的方法。
学术上那种求知、探索
敢于大胆直面人生
陈思和:我们以前是看思想性,艺术是顺带的,认为“思想好了,艺术也就上去了”。我1980年左右在复旦读书,跟李辉研究巴金,1982年完成第一部著作《巴金论稿》,当时谈的都是思想的东西——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等等,基本没有涉及巴金的艺术讨论。书稿完成,李辉说要不要写艺术方面的,我说我来写。我1982年春节一个寒假写出来。这篇文章中我通读了巴金所有的作品,给巴金划分了一下艺术演进的过程、艺术风格的改变。我注意到巴金后期三部小说风格改变的源头是在“激流第三曲”的《秋》。
我当时提出一个很新的观点,我认为巴金的风格从早年到后期有很大的变化,转折点是《秋》。《秋》那种自然主义的艺术表达方法,跟早年的观念领先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巴金的《秋》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不够,因为我们太喜欢战斗了,《家》比《秋》更具有战斗性。我这么写心里有点不安,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会不会受到批评。后来上世纪80年代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原来夏志清也是这么说,海外这么权威的学者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心就比较安了。当然艺术上什么好什么不好,这个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理解了夏志清先生对艺术的标准,那种让艺术从强烈的政治情绪中脱离出来,还原成相对来说比较沉着、比较纯粹审美的追求。
夏济安先生的书,我当时读的时候不太理解,但是我喜欢他对鲁迅心理的分析。到今天这一切都不神秘了,但我读的时候蛮震动的。夏氏兄弟在学术上那种求知、探索、敢于大胆直面人生,我是很赞赏的,也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
说到对中国作家的发掘,沈从文没有夏志清也会成为一个大家喜欢的作家,张爱玲如果夏志清不讲,中国发展到今天也会用正常的心态理解。但是在当年我们尚处在比较蒙昧的状态下,夏先生对他们那种大胆的评价、热烈的称颂是振聋发聩的。夏先生说过“我也追捧张天翼,张天翼是左翼作家,我不是从政治出发,我只是从艺术出发”。夏济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对台湾作家的培养也是善莫大焉。
文学史上,夏氏两兄弟是绕不过去的两块碑。很高兴看到夏氏书信五卷本全部出齐,大家好好阅读研究,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资料和信息,也使我们对当时海外汉学筚路蓝缕的状态有更深的认知。
18年,663封,总字数116万字
漫长岁月里两位年轻学者的通信
王德威:夏氏兄弟在西方汉学界,尤其在推动现当代文学以及明清文学研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确是筚路蓝缕,开创了西方汉学界的一个新局。我相信借由最近出版的夏氏兄弟书信集,随着这些书信第一次在海内外公布,我们对于夏氏兄弟无论是在学术史、知识史上,甚至文化史以及情感史方面都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我们重新评估夏氏兄弟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又多增添了一层向度。
以下我的发言只作为一种铺垫,说明我个人对夏氏兄弟书信集阅读之后的一些心得。
夏氏兄弟书信集整个的规模有多大?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陈述。书信集始于1947年11月21日夏志清拿了北大所提供的理事奖学金到美国深造,在他的邮轮抵达夏威夷的前一天,他给他的哥哥夏济安先生(当时仍然在北京大学任教)发的第一封信。书信集的结尾是在1965年2月19日,夏先生当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给夏济安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夏济安先生永远不能收到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因为脑溢血中风,在1965年2月23日过世。
过世之后夏志清先生从纽约赶到伯克利所在地旧金山处理后事,短短时间整理了夏济安所保留的兄弟之间的通信。这些信夏济安先生一共收到311封,而夏济安寄给夏志清先生的有352封,总数是663封。书信正文总字数116万字,再加季进教授和他的团队共同所做校注等累计字数23万字,整个夏氏兄弟书信集总字数超过140万字,分为五卷,在海峡两岸三地出版,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工程。
1947年到1965年是所谓冷战的年月,这一对兄弟天各一方,坚持通信18年,而且双方都很珍惜对方的来信,将这些来信一一保存。以我个人非常有限的经验来看,这样的绵密通信以及完整的保存,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或者文学史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当事人夏氏兄弟如此珍惜他们彼此的通信,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其中隐藏的深意。
夏济安先生生于1916年,1965年突然过世,当时还不满50岁。夏志清先生生于1921年,2013年过世。这其实是漫长岁月里两位年轻学者的通信。当夏志清1947年离开中国上海的时候,他只是一个26岁的年轻研究生,即将到美国深造。而夏济安先生经历了战时从上海到西安、昆明,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上海,再到香港、台湾,最后到美国的西雅图以及伯克利,这是他从31岁到49岁的一段历程,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这么长的时间段落说明,这些信件所承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陈思和先生在前些年曾经提到,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有知识分子以比较隐秘的方式写下当时的心路历程,所谓“抽屉里的文学”。今天看待夏氏兄弟的书信来往,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箱里的文学”或者“行李箱里的文学”?这18年里,这两位兄弟不断地在行旅过程中,夏志清先生离开上海之后到了美国,先后在伯克利、耶鲁大学,之后又到密西根大学,再到得州一个比较小的大学,又到匹兹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么漫长动荡的生命旅程里面,双方都把他们既往的信件珍而视之。夏志清晚年自述平生最希望完成的两件事,一是整理和张爱玲的通信,这些书信在2013年已经完成出版;另一件大工程就是和哥哥夏济安先生的通信,这个通信的过程更为漫长,而且内容更为丰富。
人生得一知己足以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王德威:信不只是白纸黑字,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18年里两个兄弟天各一方相互信息不断,用最薄的航空信纸或者便笺互通有无,而且以通信作为相互信守、信赖的兄弟之情以及知己甚至同行之情的表达,信在这里是一个信物。而经过通信内容所表达的种种观点,无论从政治上到爱情上,或者是家庭上、历史上,说明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到中壮辈的知识分子,离散海外之后所抱持的想法和观念,甚至,一种信念。
在阅读大量信件的过程里,我个人有以下几点观察。
首先,是这两位兄弟的书信集在广义文学史、文化史或者是知识史上的位置。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历史的论述,强调的是所谓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时代。这个时代里面有多少伦理,就有多少的期许和兴奋;有多少的涕泪飘零,就有多少的欢呼呐喊。阅读夏氏兄弟的书信,感觉两位通信者似乎深陷在历史的漩涡里,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历史,是感同身受的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是日常生活中各种细节所累积出来的历史。这样的历史70年之后重新阅读,让我们了解到这可能才是真正千千万万人所呈现于中的一种历史的洪流,有轻有重,如今一起都再次来到我们的面前。
而这个历史,是一种季进教授在他的编后记里提到的“友情的历史”。“友情的历史”不只是因为夏氏兄弟对于当时历史事件或者是个人经历或大或小的反映,有的时候微不足道,有的时候捶胸顿足,但是都代表了两位青年的海外知识分子在漂流过程当中,重新取得梳理他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彼此,还有对彼此欲望对象的各种各样的情感的认知,或者是我在这里所谓的“情感的教育”。
在这些信件里面,我们发现大量夏济安或者夏志清对自己感情的分析、对历史的评断,尤其对他们所任教的学校或者是从事的专业项目各种各样的反省、批评、观察等等。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个认知模式的观点,我想的确和当时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书写方法有非常大的不同。
而最后,我认为这些信件所代表的一种无时无刻不把历史、情感、知识,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无论是所谓雄浑而庞大的家国的感触,或者是最微妙、最细小的,甚至有点苟且的各种情感的黑暗面向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的书写。看待夏氏兄弟的书信,我们突然了解到原来在他们写作学术著作的同时,还有这么多需要他们兼顾的甚至是烦心的种种大小事物。
我总结个人粗浅的报告,容我大胆地用鲁迅送给瞿秋白的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夏氏兄弟所真正的呈现的手足之情,是我们看待现当代的中国文化史、情感史以及知识史上少见的一个范例。他们两个人这样一种所谓的推心置腹的知己之情,令我们羡慕。包括今天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场的诸位来宾,我们又何曾没有这样的愿望,希望在我们个人生命里有这样的哥哥或者弟弟,也能够有这样的朋友或者知己,坦然无私地交待自己各种各样的心事,而且一同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加诸我们种种不可思议的压力和挑战。
我引用夏师母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夏志清先生在哥哥过世以后,他再也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我们都知道夏先生是妙语如珠,甚至所谓的“人来疯”“老顽童”等等,但是又有多少机会了解到他内心彷徨、幽暗的一面?他固然继续个人的学术之旅,但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写信给他的哥哥。整理/雨驿